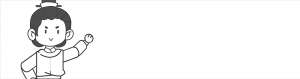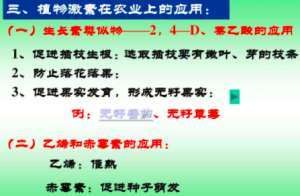海葚子种植(家乡的土地)
时间:2024-03-09 02:58:50
点击:次
我的家乡---沧县大白塚村。

白塚村土地多,在附近是众所周知的,白塚村土地盐碱,没有树木,也是出了名的。村庄周围都是大开洼,最近的村也相距十余里地。
不知什么时候流传了一个笑话,说:一只知了想飞到白塚去,半路上飞累了想歇一歇,结果没有找到一棵树落脚,最后,趴到荆条墩底下哭了一包。虽然只是个笑话,可自从这个笑话传开,周围四里八庄的大姑娘谁也不愿意嫁过来了。当然,不是因为找不到树了而是看到种不完的地,受不完的累,不愿意来了。
我是土生土长的白塚人,这片土地承载了我成长的经历和深切的感受,让我永远的留恋。
第一洼 东洼地

东洼地是最盐碱的,生长着成片的黄菜和碱蓬。黄菜和碱蓬是最耐盐碱的植物,嫩绿的时候人们都可以食用,还具有促进新陈代谢和减肥的功效。待到秋凉的时候,它们就会由绿转红,由浅变深,最后满洼地火红成一片,像极了大红地毯,很是壮观。
我是真心得感谢这块土地的贡献,因为每天打猪菜我都向她来索取。那时候,我们小孩子都要帮助家里干活,最主要的活儿就是喂猪。现在的孩子们是不干这样的活儿了,我们那时候可是干劲十足,因为年底是要用猪来换取新鞋新衣服的。
这片土地,人们多是种一些向日葵一类的耐碱作物,哪里适宜就在哪里种,花花点点的,既不成片,也不成形状,倒像是给一幅画作些点缀一样。
我最喜欢和大人们去那里干活,因为那里有很多座大盐台子可以玩。
盐台子是老辈人晒盐留下的,当时的人们挖池子,放水,然后刮碱土溶于水中,依靠太阳的热力蒸发水分,待盐结晶而出。这样得到的盐,杂质多,味苦,人们称作“小苦盐”。家乡人就是这样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,一代代生活过来的。
现在,晒苦盐早已废止了,多年的雨水冲刷,台子已经非常平缓了。台子上寸草不生,平整而柔软,细小的盐粒在阳光下烁烁闪光,像无数的珠宝一样。我经常光着脚踩在上面,非常舒服,或是翻跟头,或是挖地道,玩得开心。尤其是学骑车子时,不知摔倒过多少回,身体碰到盐碱土不会磕出一点伤来。
那时野地里有很多小动物,有一种叫作蝎虎的,四脚爬行得很快。我经常把它捉来,然后在盐滩上摁住它的尾巴,它就会迅速地断掉尾巴逃之夭夭,我知道这是它逃命的技巧,也不会去追逐它,而是看那尾巴在原地不停地摆动,甚是新奇好玩。
其实,最让我回味的是那海葚子,在盐碱滩边成片的生长铺撒开,果实是球状浆果,大小如红豆,幼果淡绿象珍珠,随着生长颜色由绿变黄,再由黄变橙红、紫红,完全成熟后为紫黑色。海葚子味道酸甜,土地越碱味越浓,即摘即食,非常好吃。海葚子成熟时候,我每次回去都吃个痛快,以至于满嘴都是紫红色的汁液。
第二洼 南洼地

这是我们村最低洼的一片土地,丛生着水草和稗草,雨季的时候经常水流成片,淹没了田地和道路,庄稼是十年九涝。
村民们在此地种植苘麻和高粱。种植苘麻主要是为了取其茎皮,这需要将苘放在水塘,然后沤熟,再剥皮。苘麻的茎皮可以织麻袋、搓绳索、编麻鞋。高粱是叫作“水里站”的品种,植株四、五米高,抗碱耐涝。这种作物产量低,但是它的作用可不小,秸秆可以扎成把子,用于村民盖房铺顶,高粱瓤可以绑笤帚,非常好用,高粱茬是很好烧的柴禾,村民用它生火做饭。
因为地势低,很多雨水大的年份直到秋天的时候,地里还是水泽一片,人们只能光着脚,蹚水收割高粱,高粱杆无法运出来,就丢在地里。到了冬天,水面结了冰,冰面上东倒西歪着成片的高粱杆,在残阳西下的衬托下,犹如古战场一样惨烈壮美。
我小的时候,村旁河沟总是有水,那时候有水就有鱼。每当大雨过后,河里的草鱼崽就特别多,沿着河边成群结队地游。一次,我用自制的踢网在涵洞管接鱼,草鱼崽顺着水流游过涵洞管,就进入了网兜,受水流的冲击,再也游不出去了。然后,我就用勺子将小鱼舀起来,放到水桶中。小鱼实在是太多了,一下午的时间,我就盛了两桶。回家后,母亲用面粉撒在鱼上面,然后在锅里煲干,再存放起来。那年冬天,我家吃了一冬季的白菜熬小鱼,味道香极了。
说道冬天,南洼地可是我们小孩子们的乐园,我和小伙伴们放假就到这里来玩。我们一起在厚厚的干草甸子上追逐、河里溜冰、趟兔子、烧荒(现在保护环境,政府不允许的)、逮野鸡,有时还在冰面里砸出鱼来,烧烤着吃。
第三洼 西洼地

西洼地的面积最大,是我们村的主要产粮区,而且大多为红土子地,村民以种植小麦、玉米、大豆为主。因有一条长河经过,河堤上的土质沙性好,所以村民们在上面种植的作物种类也很多,有芝麻、花生、红薯、胡萝卜、黍子、绿豆等。
红土子地含铁量高,粘性大,易湿也易干,墒情变化快。土地过湿时粘度大,锄到地上象面团一样,有劲使不上,过干时硬度大,锄到地上象火石一样,震得胳膊发麻,都不易耕作,所以人们在西洼地干活时,经常携带着牲口的草料和人的干粮,一干就是一天,抢墒耕作。
割豆子的时候,都是父亲在前面挑铺子,我和哥哥在后面紧跟着。有时候我累得直喊腰疼,父亲就会说:小孩子哪里有腰呀,还没有长呐,快点割吧。我知道这都是大人骗小孩子的话,可没有办法,那时候人们都是没黑没白的干活,看父亲已经佝偻的身子,就知道生活不容易。
收割完豆子,是我最兴奋的时候,我要“清剿”田鼠洞。田鼠在豆粒成熟的时候,将豆子运进洞中储存起来,以备过冬。我们辛辛苦苦一年的劳作,它却坐享其成。鼠洞有一米多深,分为卧室、厨房、玩耍间、储藏间和厕所。它过得可比我滋润,我常常这样想,抓住它一定为民除害。一只田鼠多的时候可以储存百八十斤大豆,有几只田鼠在你地里,准会叫你丰产不丰收,所以每当我挖出大豆来,消灭了田鼠,就会觉得非常的高兴和过瘾。我挖洞的时候,先将一把干草点燃,塞进洞口,然后向里面吹气,看能有几处冒烟,那都是田鼠的逃跑“后门”,一定要堵死,随后再挖,来个“瓮中捉鳖”。
一次,我发现了一个大洞,估计是只硕鼠,心想一定会收获不少粮食。我按以往的经验,堵住它各个逃跑的洞口。挖到一米深的时候,看见一只大田鼠探出了头,我急忙用铁锨朝它的头铲去,这家伙一缩身退回了洞中。我继续沿着鼠洞向下面挖掘,这只田鼠探头越来越频繁了,每次它都能机敏地躲过我的锨头。我知道距离洞底不远了,它将无路可退。正在我弯着腰用力刨着土的时候,这只大田鼠突然从洞中弹跳而出,吱吱地叫着向我眼前飞来,只差一点就咬到我的鼻子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凶猛的老鼠,被它咬了个措手不及,吓得我转身托着铁锨就跑。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,田鼠一跳一跳地玩命地追着我跑,眼看就要咬到屁股上,顾不了其它的了,我丢掉铁锨,撒丫子一口气跑出去一百多米,回头看不见了田鼠,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,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,心想:这他妈的是谁剿灭谁呀!
第四洼 北洼地

北洼地碱薄,却有着大片的芦草,它生长在水沟边茎粗杆直叫芦苇,生长在地里株矮叶尖叫芦草。
人们在这里种植棉花和杂交高粱,然而芦草可是让庄稼人吃尽了苦头,本来土地就贫瘠,它还赖在地里疯狂地生长,与庄稼争夺养料,你昨天刚把它铲除,今天又很快长了出来,它的根系发达,长达七、八米,让你想除恶务尽,但总是事半功倍无可奈何。
你要认为芦草是这块地的狠角色,那你就错了,更可恨的是牛虻(我们叫它瞎虻)。我小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这块地牛虻的演变,一开始的时候,是苍蝇大小的花翅牛虻,然后出现了蚕豆大小的大眼绿色的牛虻,再后来是一种黑色的大个牛虻。我是分不清它们的种类,只知道后来的牛虻嗜血性更大,攻击力更强,它们专吸牛马等厚皮动物的血,很少攻击人类。
牛虻就生活在芦草洼里,基本不作迁移。每天早晨在太阳升起来,草叶上的露水落下后开始活动,到那时候整个的大洼都嗡嗡地作响,甚是恐怖吓人。人们到北洼地干活,都是趁着清早,在露水快要落下以前赶紧撤离,以避免牲畜被牛虻攻击。
记得我和父亲有一次想把活儿干完,离开的晚了一点,洼里牛虻起来了。开始的时候,我还可以用手拍打落在牛身上的牛虻,不到十分钟,成群的牛虻就围攻了上来,我急忙折了些荆条,在牛的身上轰赶着,可是这群刚被赶起来,那群又扑上来。这时牛被叮咬的不再温顺,猛烈地晃着头,呼扇着耳朵,不停地甩着尾巴,两条后腿不住地踢踏,难受极了。我看到我家的黄牛一会的功夫,全身落满了牛虻,竟变成了一头黑牛。我伸手使劲地打了下去,一手的牛虻死尸,同时鲜血顺着手指往下淌。父亲说了一声:快走,牛车都没要,我们和牛飞奔出了芦草地。等到逃上了大道,牛虻不再追击,陆续的飞回了“基地”。牛的身上已是伤痕累累,全身都是疙疙瘩瘩的大包,很多地方还在流血,顺着牛毛染红一片。老牛回到家身体一直哆嗦着,我心疼得揪成了一个,这是我见到的最惨不忍睹的一回。
第五洼 沧东工业园

沧东工业园是2011年成立的省级开发区,她是以白塚洼地为主要开发用地的工业园区,已纳入沧州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战略。现在,已经引进了上百家企业,尤其是明珠服装特色小镇已初具规模,远近客商闻名而来络绎不绝。
以前的盐碱地焕发了她新的生机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鳞次栉比;交通公路四通八达,宽阔平坦;草木绿化郁郁葱葱,美丽井然。
沧东工业园的建设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巨大的效益,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,告别了白塚人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落后的面貌,户户都盖起来了楼房别墅,人人都开上了轿车,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。
家乡的土地,流年笑掷,未来可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