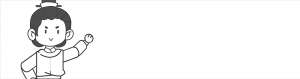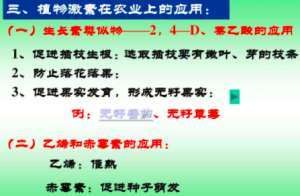天井里的种植答案(从控江新村溢出的水流)
时间:2024-01-12 15:18:09
点击:次
如何区别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节日?有时,亮几盏灯就够了。
黄昱宁幼时,家住杨浦区控江新村,家对面就是上海光学仪器一厂。遇到节日,有时厂里会把厂区内所有的灯都打开。家长抱着小黄昱宁去看灯。周边的居民也都如此。围着工厂,大人孩子们的眼睛和脸都被照亮,大家一起欣赏墙内的亮光,庆祝节日的到来。这幅颇具工业化风格的场景,被染上生活的气息。
昔日的上海郊区江湾,遍布厂房。1951年上海市政府规划9个住宅基地,先后建造了曹杨新村、长白新村等18个工人新村。控江新村,也在当时应运而生。相比老式石库门的狭小居住空间,控江新村的房间虽然不大,但有相对独立的煤卫设施,小区里有整洁的花园和新栽的小树。原先住在虹口区明华坊的黄昱宁外婆一家,将家里的房子调换到控江新村。1975年,黄昱宁在这里出生。
几年后,改革开放。国门打开,计划经济年代进入尾声。浪潮袭来,影响了整个城市,影响了产业工人的生活,也影响了生活在工人新村的黄昱宁。她所熟悉的这一方上海,如被大雨涨满的池塘,溢出的水流漫延向前,和其他区域的上海融合在了一起,汇成了一个新上海。
新村里的书柜

在工人新村建成之前,上世纪50年代,许多沪东地区的工人住在阁楼上、亭子间、草棚子里,甚至于住在破船上。能住进整齐有煤卫设施的新村,不仅居住条件改善,而且更觉得到尊严。不过,工人新村的住户也不全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。黄昱宁的外祖母毫无重男轻女的偏见,看见长女读书优异,毅然供她去大学深造。等到长女成婚,又一直和长女生活在一起。因此,从黄昱宁记事起,小时候的控江新村,是个外婆当家做主、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母系社会。
黄昱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,与大学同学结婚。当时,毕业听从分配,母亲去上海仪表局下属工厂担任技术翻译。父亲因为是广东人,被分配回原籍工作,只能在节假日和寒暑假回上海与妻女团聚。但即便每年相逢的日子短暂,黄昱宁的父亲还是在控江新村的小房间里打造了一具书柜。为了做好书柜,他每次回上海,还会特意带来些广东的板材。一块木头一块木头彼此咬合。这具最终由父母精心打造成的书柜,是在黄昱宁的记忆里,同龄人和邻居家里从未出现的家具。书柜里如此大的藏书规模,也是同龄人和邻居家里从未有过的风景。
在工人新村的知识分子家庭里,黄昱宁几乎是自然而然长成了一个读书种子。她在游戏玩耍项目上显得笨拙,但对于读书却始终乐在其中。
放下书本的时候,父母会带她往五角场方向散步。穿过几条大马路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?离开控江新村不过15分钟步行之外的世界,当时还是一片郊野。今日车水马龙的五角场商圈周边,当时有过人头高的芦苇、野草,刺猬和黄鼠狼出没其间。小黄昱宁在父母背后好奇地伸出头去,能看见当地农人养着的猪。这个尚未被城市化的地方,显露出一种未被驯服的野生感,叫小女孩觉得好奇也畏惧。她更不常出门闲逛了。穿越大马路如一项可惧的挑战,让她心里隐隐有不安。她把头埋在书本里。
洼地之变

1985年8月1日,上海暴雨,9200多户居民家中进水,最深的达80厘米。其中,控江路、延吉路之间的双阳路周围一片汪洋,积水深度平均达到50厘米。控江地区由于地势低洼,加之历年来新村规模不断扩大,相应的排水系统没有跟上,一场大雨过后,2千多户居民家中进水受淹。黄昱宁还依稀记得,外公在他们一楼房间外的天井里,种植的蔷薇、枇杷、丝瓜藤都被大水淹得岌岌可危,平日圈养的几只鸭子,此时高兴地在积水里游起泳来。
次日的《解放日报》记载了发大水当天中午,市领导涉水到控江地区察看马路积水情况,还到控江三村看望慰问了两户进水居民。得知此地正在新修下水道工程时,市领导要求防汛指挥部的领导“要把防汛排涝工作,作为重点抓,这方面的工程要迅速上马,该花钱的地方一定要舍得花。”
这年9月26日,作为本市居民住宅区的一项大规模排水工程,控江地区排水工程启动。这也意味着,这一地区八万多居民在日后汛期来到时,将免受水淹之苦。
门外的世界

和新修的排水工程一起来到控江新村的,还有外婆失散多年的兄弟,黄昱宁的舅公。
1983年的一个下午,一个戴着鸭舌帽、穿着当时上海鲜见的格子夹克衫的老头,走进黄昱宁家。原来,外婆家的男丁,新中国成立前都子承父业担任太古轮船上的船员。1949年太古关闭了上海办事处,舅公就跟着公司去了香港,几年后与上海的家人断了音讯。
几十年后,这位舅公的忽然出现,似乎忽然打开了控江新村面向外部世界的窗户。原本,黄昱宁所有的亲戚都住在控江新村周边,她在附近上小学、走亲戚,几乎从不涉足控江地区以外的地方。舅公和他家人的陆续来访,让黄昱宁有机会陪着客人到了“另一个上海”——一个由外滩、东风饭店、大世界构成的上海,一个更常被影视作品描述也更为外地游客熟悉的上海。
她陪着大人们挤公交、坐出租车,见识这些于香港游客是重温故地、于她这个上海人却是新鲜事物的场景。她听着饭桌上阿姨舅舅们热烈讨论着换外币、经济担保、出国等等词汇。
阵阵新风扑面。城里涌动着渴望改变的气息。外婆去香港探亲,回家后为黄昱宁带来小小的金坠子、米老鼠图案的运动套装、随身听、自动照相机、邓丽君的唱片……原来,控江新村外有一个上海,上海外有一个香港,香港外有一个世界。
和亲戚们的观念一起发生改变的,还有母亲的工作环境。原本母亲在厂里担任技术翻译,每日的生活平平无奇。骤然之间,外宾来访,海外交流频繁,母亲不仅需要在案头翻译,还要为厂里的外事工作担任口译。参与到接待外宾的工作,让母亲最后几年的工作生涯变得丰富灿烂、眼界大开。这种内心的小小优越感一路升高,直到整个城市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,工厂效益下滑,工人们开始下岗。
终于有一天,母亲对当时已经调到上海一所中专任教的父亲感慨:还是做老师好。
多多少少受时代风潮的影响,黄昱宁在高中毕业后升入上海外国语大学。全家也搬离了控江新村。在大学里,黄昱宁遇到不少上海“上只角”出身的同学,这些格致中学、向明中学、位育中学毕业的学生,和黄昱宁说着一模一样的上海话,但对上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。
他们熟悉的阡陌交错的弄堂、沿街琳琅满目的小店、商业街的繁华和热闹,于黄昱宁而言,都是陌生的。黄昱宁熟悉的规整的新村住房、曾经探险过的农民猪圈、宽敞的中小学校园,对住在闹市区习惯了逼仄环境的同学们而言,也是陌生的。
黄昱宁进入大学的上世纪90年代,上海开始进入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,区域之间的差异被缩小抹平。但很多年后,黄昱宁还是有点害怕过大马路。她做梦回旧居,梦到这间位于控江四村底楼的小屋,梦里的空气总是潮潮的,梦里的水门汀地板总是湿漉漉的。

黄昱宁提供
黄昱宁,1975年出生于上海,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、编审,《外国文艺》杂志主编。译有《甜牙》《追日》《在切瑟尔海滩上》等,译著近三百万字。
栏目主编:沈轶伦 文字编辑:沈轶伦 图片编辑:项建英
建筑摄影:邵竞